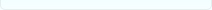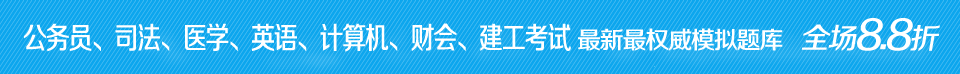[說明]:閱讀是一個(gè)經(jīng)久不衰的話題,從古至今,人們對(duì)閱讀的熱愛,或?yàn)榍笾⒒驗(yàn)槊⒁嗷蛘呤亲穼ひ惶幘竦臍w處,種種原因,不能細(xì)究,繼續(xù)前面兩個(gè)閱讀話題:《閱讀的實(shí)用與無用》,《閱讀的求職與反智》,本文將從閱讀本身、閱讀者、民族精神以及人類文明等方面來探討本系列的最后一個(gè)話題:閱讀的意義與去意義。
閱讀的意義何在?這是一個(gè)見仁見智的問題,如果讓底層民工、全職太太、高考學(xué)子、宣傳部長(zhǎng)和哲學(xué)教授就此作答,給出的答案可能大相徑庭。畢竟每一個(gè)人的閱讀各有其需。不過,閱讀終歸屬于在語(yǔ)言符號(hào)中“尋找意義”的精神活動(dòng)。正如網(wǎng)上流傳的一段話所說:“買書、讀書是世界上門檻最低的高貴舉動(dòng)。只要付出一個(gè)漢堡的錢,便可以得到一個(gè)作者在一段歲月乃至一生中的思想、知識(shí)與體驗(yàn)。”閱讀需要理解、感悟書中的思想、知識(shí)和體驗(yàn),在“熏、浸、刺、提”的閱讀過程中,受到真、善、美的化育。無論對(duì)于個(gè)體還是民族而言,閱讀都是有意義的。
就閱讀者而言,個(gè)人的精神發(fā)展史,可以說就是其閱讀史。閱讀讓個(gè)人脫離現(xiàn)實(shí)的束縛和限制,在吮吸知識(shí)乳汁的同時(shí)翱翔于符號(hào)構(gòu)筑的奇異世界。茨威格在《書的禮贊》中寫道:“一個(gè)人和書籍接觸得愈親密,他便愈加深刻地感到生活的統(tǒng)一,因?yàn)樗娜烁駨?fù)化了:他不僅用他自己的眼睛觀察,而且運(yùn)用著無數(shù)心靈的眼睛,由于他們這種崇高的幫助,他將懷著摯愛的同情踏遍整個(gè)世界。”林語(yǔ)堂也說:“沒有
閱讀習(xí)慣的人,就時(shí)間、空間而言簡(jiǎn)直就被監(jiān)禁于周遭的環(huán)境中。……但當(dāng)他拿起一本書,他立刻就進(jìn)入了另一個(gè)世界。”圖書作為人類保
存記憶的一種裝置,作為人與人深層溝通的橋梁,具有超越時(shí)空的力量。然而,這種力量的獲取,需要讀者與作者心智的深層互換,需要讀者安靜下來細(xì)細(xì)品味。隨著社會(huì)的發(fā)展,國(guó)民的閱讀總量呈上升趨勢(shì),但閱讀內(nèi)容和閱讀方式卻阻抑追尋意義的熱情。
從民族精神來看,我國(guó)素有“耕讀傳家”的優(yōu)良傳統(tǒng),重視知識(shí)和道德的傳承。一部漫長(zhǎng)的中華文明史,就是一部圖書史。實(shí)際上,閱讀不僅是個(gè)人行為,也是民族精神的積累行為。在知識(shí)爆炸和競(jìng)爭(zhēng)的時(shí)代,閱讀更是具有“民族戰(zhàn)略”的意義。美國(guó)將“閱讀優(yōu)先”作為教育政策的主軸,日本把書店叫做“文化的街燈”,法國(guó)建立“讀書沙龍”讓讀者受益,英國(guó)要打造一個(gè)“讀書人”的國(guó)度,韓國(guó)把閱讀當(dāng)做是國(guó)民教育的一環(huán),印度提出“請(qǐng)我吃飯,不如送我本書”的交朋友原則等等,這一切均有國(guó)家戰(zhàn)略的考量。作為國(guó)家戰(zhàn)略的閱讀運(yùn)動(dòng),自然以完善、提升民族整體素質(zhì)為目標(biāo)。
從人類文明的發(fā)展來看,圖書典籍的誕生,改變了脆弱的口耳相傳的知識(shí)傳承系統(tǒng),使文化有了穩(wěn)固的載體。甚至有人認(rèn)為,書與人,人與書,就構(gòu)成了一個(gè)個(gè)文明。愛迪生也曾說,書籍是天才留給人類的遺產(chǎn)。書籍讓一代代人不斷站在巨人的肩膀上,人類文明方才有了不斷向前發(fā)展的可能,因而也可以說,沒有閱讀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人類文明。
閱讀作為從文本的語(yǔ)言符號(hào)中獲取意義的心理過程,并非光靠手和眼睛就能完成,無論會(huì)意還是頓悟,都表明意義的“獲取”需要用心用腦。閱讀者通過體悟來內(nèi)化典籍的智慧和道德,才能知書達(dá)理,博古通今。司馬遷著《史記》,意在“究天人之際,通古今之變,成一家之言”,讀者只有用心閱讀,方能體會(huì)其意。然而,在迷戀功利性和娛樂性閱讀的時(shí)代,浮躁的人們無暇也無心追尋高深的意義,文本的制造者亦不愿自找沒趣,因此充斥耳目的是快餐文化。其結(jié)果是,閱讀行為逐漸與道德教化、人格養(yǎng)成疏離,閱讀所具有的智慧交鋒和美的熏陶
的效用亦被削弱。人們開始抱怨魯迅的作品太艱澀,經(jīng)常指責(zé)學(xué)院派的批評(píng)玩高深,現(xiàn)在也沒有多少人愿意讀完《存在與時(shí)間》,因?yàn)樗麄儾辉纲M(fèi)事去揣摩文本的“意義”,他們寧愿點(diǎn)一份快餐文化放松一下。
去意義的閱讀習(xí)慣和思維模式穩(wěn)固之后,人們就會(huì)懈怠于自己在社會(huì)中所扮演的角色,將求學(xué)階段的讀書當(dāng)成“應(yīng)付”,將工作以后的閱讀當(dāng)成“消遣”,從而遠(yuǎn)離了閱讀應(yīng)有的意義旨?xì)w。不健康的閱讀趣味和習(xí)慣,以及對(duì)閱讀意義的忽略,有如傳染病菌一樣,在人群中擴(kuò)散,讓人群交叉感染,從而成為一種流行病、時(shí)代病。
每個(gè)人選擇閱讀什么樣的書籍,采取什么樣的
閱讀方式,他人無從干涉。但是,并不意味著良性引導(dǎo)可以缺席。時(shí)下國(guó)家將“全民閱讀”寫入政府工作報(bào)告,在各地不斷開展讀書日、讀書周、讀書月的活動(dòng),無疑是出于重塑閱讀精神和閱讀品格的需要。
數(shù)字媒介的興起,讓人們結(jié)束了枯燈照壁的冷寂,也告別了登高望月的雅致,但千百年來閱讀所固有的精神品格仍未終結(jié)。一方面,契合時(shí)代節(jié)律的現(xiàn)代閱讀正不斷在實(shí)用、反智與去意義的荒漠里艱難跋涉;另一方面,對(duì)知識(shí)的渴望,對(duì)審美的追求,對(duì)閱讀意義的追尋和對(duì)閱讀精神的堅(jiān)守,仍留存于每一個(gè)人的內(nèi)心深處。閱讀何去何從,值得每個(gè)人認(rèn)真思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