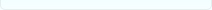閱讀有很多方法和技巧,閱讀時學會提問,無疑是很重要的一種方法。古人說:“學貴有疑,小疑則小進,大疑則大進。”今天我們來聊聊閱讀時如何引導孩子或者學生提出問題,從而走向文本深處漫溯,并成為獨立的閱讀者。
幼兒園和小學階段,課堂上常常是“叢林”現象,可以看到孩子們爭先恐后地舉手提問或回答問題,在家里孩子好像也總有問不完的問題。到了初中,孩子就很少愿意提問、回答或者主動提問,到了高中,無人提問的情況更甚,課堂成為了“戲堂”,常常教師一個人唱著獨角戲,自問自答,學生觀看而已。
所以,有專家在中西方教育的比較研究中曾說:中國衡量教育成功的標準是:將有問題(不會)的學生教育成沒問題,全懂了(學會了),所以中國學生年齡越大,年級越高,問題越少;美國衡量教育成功的標準是:將沒有問題的學生教育得有問題,如果學生提出的問題教師都回答不了,那算是非常成功,所以美國學生年級越高,越有創意,越會突發奇想。
講個現象級的故事,是關于猶太人如何重視孩子提問的故事。
猶太人是一個特殊的民族,他們人口不多。從諾貝爾獲獎的比例上看,他們獲獎的比例也實在是高的嚇人。在歷史上,至少有201位猶太人或是有二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三猶太血統的人士,曾獲得諾貝爾獎,占據了從1901到2017年世界范圍諾貝爾獲得者總數的23%。毫不諱言,如果沒有猶太科學家,人類的文明發展可能要被大大地拖后了。
猶太教育的精華之一,就是培養善于提問和質疑的孩子。他們的孩子,從小就是在提問中長大的。有個猶太人曾這么說:我小時候,每天回家,我爸都會用相同的一句話來和我打招呼——你今天提出了什么樣的問題?我爸從來不問我那天學到了什么,他只在乎我是不是能保持好奇心。
后來我才明白,原來提問的能力和
學習的能力是息息相關的,因為如果你沒有掌握新的知識,沒有積極動腦思考,你就提不出新問題,也提不出好問題。
學會提問的背后是好奇心,對世界萬物的好奇心,在提問中不斷突破原有的思維結構,持續升級認知系統,增加創新發明能力。美國著名學者布魯巴克也很精辟地指出:“最精湛的教學藝術,遵循的最高準則就是讓學生自己提問題。”
換個語境,借個地方說話,在閱讀領域,提問也是最高準則。什么是高質量的閱讀?重要的標準之一就是在閱讀過程中,讀者隨著文本的演變和推進不斷提出問題。提問的過程是對話的過程,讀者與文本對話,與作者對話,與自我對話,是讀者向文本更深處漫溯的過程。
如今我們經常在強調閱讀中的批判性思維,什么是批判性思維?這是一種質疑和求證的能力,一方面具有判性思維的人在面對問題時不會輕易接受既有結論,而是會進一步對問題進行深入思考,評估問題的深度、廣度以及邏輯性,從而得出自己的見解。更為重要的是在于理性思考和
獨立思考,能夠對于身邊的現象和事物提出問題。
閱讀中孩子問題意識的培養和問題提出能力的培養,是閱讀中批判性思維培養的起點。如果一個孩子只是跟著文本情節“隨波逐流”,全然沒有自己的思考、全然沒有聯系自我的個人生活經驗,只是在文本的表層滑行,當然無法引領學生走向文本靈魂的深處,就更不必談與文本,與讀者等開展積極的對話,批判性思維更無從談起。
培養孩子在閱讀中提問和對話,其實也是培養孩子良好的閱讀習慣和方法。一個終身的閱讀者一定具有其獨特閱讀密碼和閱讀方式,但是所有喜歡閱讀的人都是會思考的人,思考的過程就是提問的過程,也就是在閱讀過程中不斷在文本本身和個人經驗建立聯系,浸入文本,并生成新的理解和體會的過程。
一個在閱讀中不斷探索意義,塑造自我的閱讀經驗的人,勢必會成為終身的閱讀者,也是閱讀個性化的體現。
其實,提問在一定意義上是閱讀元認知的方法和策略,什么是元認知?這是布魯姆認知目標分類法提到的人類的第四種知識。具體體現為了解、檢驗、評估和調整自己學習的策略,是對認知活動進行反思的系統。
閱讀中的元認知,是對閱讀過程調試、反思和提問的過程,如何帶著準備去閱讀?如何在閱讀中破除理解障礙?如何與文本開展深度對話?等等。提問就是幫助讀者不斷調試閱讀認知,促進理解,生成個體體驗的工具。
信息化的社會,知識浪潮洶涌而來。在這樣的情形下,我們缺的不是知識、信息和書籍,而是鑒別力和分析力,在繁蕪的知識中的鑒別能力。
這樣的能力是建立在提問的基礎上,什么是重要的知識?什么是有價值的知識?這些知識與我的生活有何關聯?這些知識如何為個人的核心競爭力服務?這些提問能力同樣與閱讀有關,閱讀本身是去偽存真、去粗留精、甄別分析的過程。會提問的孩子自然具有鑒別的先導思維,質疑和修正的思維:提問自己哪些是具有價值的?哪些是不值得花時間?
在文章的開頭,談到孩子隨著年齡的增長,問題慢慢消失的現象,原因在于無論在課堂、生活還是在閱讀中,我們很少鼓勵孩子提問,提供寬容的提問時空環境,也很少鼓勵孩子去表達自己的困惑,久而久之,他們的好奇心就不會有了,探究意識很薄弱,就不會主動提問和積極思考。
六段式提問幫助學生深度閱讀
六段式閱讀提問法貫穿于整個閱讀過程,其設計的問題串聯起了問題鏈,能激發學生的提問能力和思維,從而培養學生的思維品質和
閱讀習慣。
1.讀前提問
閱讀專家一直認為閱讀前的思考和提問很重要,也就是說用問題開啟閱讀一本書或者一個故事。父母和教師應該通過建立一定的閱讀模式,如培育閱讀熱情、建立閱讀目的和激發對于文本的好奇,必然會激燃孩子內心的閱讀興趣。當然,要允許孩子選擇他們自己喜歡的書籍,這樣對話的大門才會慢慢開啟。試想,一個孩子對某一書籍絲毫不感興趣,他怎么會有提問的欲望呢?
有個研究證明,如果孩子能夠選擇恰當的材料,閱讀的準確率至少能夠達到98%。用這種方法的話,孩子會有意無意地思考他們所讀的材料,提高他們的閱讀流利度和正確率。
當孩子選好一本書后,家長就與孩子討論,提出問題,對文本開展閱讀前的探索和交流:瀏覽書的封面、標題、簡介和標題,猜猜這本書是關于什么?你是如何知道的?為什么閱讀這本書,或者為什么選這部分?你想要了解書的主題什么?等等。
2.讀中提問
具有提問和思考元認知的讀者會在閱讀過程對文本進行自我對話,這個對話對于文本理解極其重要。對話的過程是對文本不斷理解、建構意義的過程。以下是家長和老師可以鼓勵孩子提問他們自己的問題。
你閱讀的故事主要元素有哪些?什么是主要的思想?主人公是誰?配角是誰?如果是非虛構性文本,那主要表達了什么觀點,分觀點又是什么......
3.再讀一遍
當孩子閱讀完最后一行字,是否意味他的閱讀旅程結束了?當然,真正的“閱讀巔峰”是發生在學生閱讀文本結束,因為閱讀后的提問和思考更多地體現在生成和創造上,將文本經驗轉化為個人經驗。
可視化在
閱讀效果提升,培養元認知策略方面發揮著積極的作用,這是一種叫做“大腦重現”的方法。家長和老師可以鼓勵孩子閉上眼睛,想象復雜的、抽象的概念,使他們在腦海里立體化,賦予具象;還可以要求孩子去想象故事里人物形象、場景地點和情節動作等等,將故事活靈活現,在腦海里呈現出來。
在閱讀一遍之后,孩子還可以重讀一遍,這次閱讀與第一次閱讀任務和目的略有不同,如果說第一次閱讀是登山過程中對沿途風景的欣賞和瀏覽的話,細細體會文本的細節,那第二次閱讀是登上山峰的俯瞰和俯視,一覽無遺廣袤的風光。
第二次閱讀更強調的是對于文本的整體把握和再生成。此時,孩子可以借助閱讀導圖,建立故事或文本的框架結構,將文本故事里最主要的要素或支持的細節完整呈現出來。
4.總結文本
之后,總結自然是閱讀的最后環節和最高境界,是檢驗學生是否理解這個故事或章節的最佳方式,這也是文本輸出、思想錘煉的一種過程。但是總結的能力不是自然而然生成的,而是家長和老師需要幫助孩子搭建問題的支架,引導他們慢慢具有總結、分析的能力和意識。
在你讀的文章中,什么是作者最想表達的,或者什么是最重要的?文本中的“為什么、誰、什么、何時、如何”的問題是哪些?什么是故事的主線或觀點?用自己的話表達出來。這個故事(這一章)中發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?
5.評價文本
評價在教學目標范疇屬于高階能力,要求學習者獲得文本信息、分析文本內容信息,包括以自己的標準來判斷文本內容,閱讀活動中的評價也屬于高階思維,是高水平
閱讀能力的體現。
作者為什么寫這個故事?他們想讓你學到什么?你能用自己的話來復述這個故事嗎?有哪些詞匯或觀點你還不明白?你能按順序說出書(文章)中發生了什么嗎?你認為作者為何寫這個主題?解釋作者的邏輯和推理。作者的信息來源何處?
6.延伸文本
閱讀最終是為了什么?是為了對于文本客體的理解嗎?是對于文本中字、詞或句的識記和掌握嗎?不是!根本在于促進學生主體的自我建構和生命成長的目的,只有將孩子的生命體驗和精神探索與閱讀結合起來,對文本再建構和再創造,才能達到閱讀塑造人精神和靈魂的真正目的。“讀者系”問題將孩子慢慢引導他們在閱讀中與自我體會、經驗的鏈接。
故事結束以后,你覺得主人公接下來會怎樣? 你的預測是正確的嗎?為什么?這個故事(角色)和另一個故事(角色)有哪些不同?關于這個話題,你最感興趣的是什么......
當然,對話能力和提問能力的培養不是一蹴而就的,不是靠數天或者數周養成的,而是經久累月的、依靠家長和老師引導培養。而這些問題就像探險者跋涉在黑暗的隧洞里,手中舉著的火吧,幫助孩子在閱讀中突破障礙,生成體驗,獲得情感,培養思維。
來源:騰訊教育(略有刪減)
作者:鄭鋼,外灘教育特約作者,上海三林東校黨支部書記,著有《美國如何培養核心素養——走進美國校園與課堂》一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