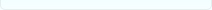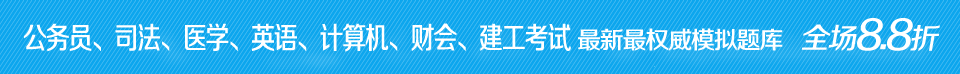說(shuō)來(lái)矛盾,我們前面所說(shuō)的讓社會(huì)科學(xué)看來(lái)很容易閱讀的因素,卻也是讓社會(huì)科學(xué)不容易閱讀的因素。譬如我們前面所提到的最后一個(gè)因素—你身為一個(gè)讀者,要對(duì)作者的觀點(diǎn)投入一些看法。許多讀者擔(dān)心,如果承認(rèn)自己與作者意見(jiàn)不合,而且客觀地質(zhì)疑自己閱讀的作品,是一種對(duì)自己投人不忠的行為。但是,只要你是用分析閱讀來(lái)閱讀,這樣的態(tài)度是必要的。
我們所談的閱讀規(guī)則中已經(jīng)指出了這樣的態(tài)度,至少在做大綱架構(gòu)及詮釋作品的規(guī)則中指出過(guò)。如果你要回答閱讀任何作品都該提出的頭兩個(gè)問(wèn)題,你一定要先檢查一下你自己的意見(jiàn)是什么。如果你拒絕傾聽(tīng)一位作者所說(shuō)的話,你就無(wú)法了解這本書(shū)了。
社會(huì)科學(xué)中熟悉的術(shù)語(yǔ)及觀點(diǎn),同時(shí)也造成了理解上的障礙。許多社會(huì)科學(xué)家自己很清楚這個(gè)問(wèn)題。他們非常反對(duì)在一般新聞報(bào)導(dǎo)或其他類型的寫(xiě)作中,任意引用社會(huì)科學(xué)的術(shù)語(yǔ)及觀點(diǎn)。譬如國(guó)民生產(chǎn)總值這個(gè)概念,在嚴(yán)肅的經(jīng)濟(jì)作品中,這個(gè)概念有特定限制的用法。但是,一些社會(huì)科學(xué)家說(shuō),許多記者及專欄作者讓這個(gè)概念承擔(dān)了太多的責(zé)任。他們用得太浮濫,卻完全不知道真正的意義是什么。顯然,如果在你閱讀的作品中,作者將一個(gè)自己都不太清楚的詞句當(dāng)作是關(guān)鍵字,那你一定也會(huì)跟著摸不著頭腦的。
讓我們把這個(gè)觀點(diǎn)再說(shuō)明清楚一點(diǎn)。我們要先把社會(huì)科學(xué)與自然科學(xué)—物理、化學(xué)等—區(qū)分出來(lái)。我們已經(jīng)知道,科學(xué)作品(指的是后面那種“科學(xué)”)的作者會(huì)把假設(shè)與證明說(shuō)得十分清楚,同時(shí)也確定讀者很容易與他達(dá)成共識(shí),并找到書(shū)中的
主旨。因?yàn)樵陂喿x任何論說(shuō)性作品時(shí),與作者達(dá)成共識(shí)并找到主旨是最重要的一部分,科學(xué)家的作法等于是幫你做了這部分的工作。不過(guò)你還是會(huì)發(fā)現(xiàn)用數(shù)學(xué)形式表現(xiàn)的作品很難閱讀,如果你沒(méi)法牢牢掌握住論述、實(shí)驗(yàn),以及對(duì)結(jié)論的觀察基礎(chǔ),你會(huì)發(fā)現(xiàn)很難對(duì)這本書(shū)下評(píng)論—也就是回答“這是真實(shí)的嗎?”“這本書(shū)與我何干?”的問(wèn)題。然而,有一點(diǎn)很重要的是,閱讀科學(xué)作品要比閱讀任何其他論說(shuō)性作品都來(lái)得容易。
換句話說(shuō),自然科學(xué)的作者必須做的是“把他的用語(yǔ)規(guī)定出來(lái)”—這也就是說(shuō),他告訴你,在他的論述中有哪些基本的詞義,而他會(huì)如何運(yùn)用。這樣的說(shuō)明通常會(huì)出現(xiàn)在書(shū)的一開(kāi)頭,可能是解釋、假設(shè)、公理等等。既然說(shuō)明用語(yǔ)是這個(gè)領(lǐng)域中的特質(zhì),因此有人說(shuō)它們像是一種游戲,或是有“游戲的架構(gòu)”。
說(shuō)明用語(yǔ)就像是一種游戲規(guī)則。如果你想打撲克牌,你不會(huì)爭(zhēng)論三張相同的牌,是否比兩對(duì)的牌要厲害之類的游戲規(guī)則。如果你要玩橋牌,你也不會(huì)為皇后可以吃杰克(同一種花色),或是最高的王牌可以吃任何一張牌(在定約橋牌中)這樣的規(guī)則而與人爭(zhēng)辯。同樣地,在閱讀自然科學(xué)的作品時(shí),你也不會(huì)與作者爭(zhēng)辯他的使用規(guī)則。你接受這些規(guī)則,開(kāi)始閱讀。
直到最近,在自然科學(xué)中已經(jīng)很普遍的用語(yǔ)說(shuō)明,在社會(huì)科學(xué)中卻仍然不太普遍。其中一個(gè)理由是,社會(huì)科學(xué)并不能數(shù)學(xué)化,另一個(gè)理由是在社會(huì)或行為科學(xué)中,要說(shuō)明用語(yǔ)比較困難。為一個(gè)圓或等腰三角形下定義是一回事,而為經(jīng)濟(jì)蕭條或心理健康下定義又是另一回事。就算一個(gè)社會(huì)科學(xué)家想要為這樣的詞義下定義,他的讀者也會(huì)想質(zhì)疑他的用法是否正確。結(jié)果,社會(huì)科學(xué)家只好在整本書(shū)中為自己的詞義掙扎不已—他的掙扎也帶給讀者閱讀上的困難。
閱讀社會(huì)科學(xué)作品最困難的地方在于:事實(shí)上,在這個(gè)領(lǐng)域中的作品是混雜的,而不是純粹的論說(shuō)性作品。我們已經(jīng)知道歷史是如何混雜了虛構(gòu)與科學(xué),以及我們閱讀時(shí)要如何把這件事謹(jǐn)記在心。對(duì)于這種混雜,我們已經(jīng)很熟悉,也有大量的相關(guān)經(jīng)驗(yàn)。但在社會(huì)科學(xué)的狀況卻完全不同。太多社會(huì)科學(xué)的作品混雜了科學(xué)、哲學(xué)與歷史,甚至為了加強(qiáng)效果,通常還會(huì)帶點(diǎn)虛構(gòu)的色彩。
如果社會(huì)科學(xué)只有一種混雜法,我們也會(huì)很熟悉,因?yàn)闅v史就是如此。但是實(shí)際上并非如此。在社會(huì)科學(xué)中,每一本書(shū)的混雜方式都不同,讀者在閱讀時(shí)必須先確定他在閱讀的書(shū)中混雜了哪些因素。這些因素可能在同一本書(shū)中就有所變動(dòng),也可能在不同的書(shū)中有所變動(dòng)。要區(qū)分清楚這一切,并不容易。
你還記得分析閱讀的第一個(gè)步驟是回答這個(gè)問(wèn)題:這是本什么樣的書(shū)?如果是小說(shuō),這個(gè)問(wèn)題相當(dāng)容易回答。如果是科學(xué)或哲學(xué)作品,也不難。就算是形式混雜的歷史,一般來(lái)說(shuō)讀者也會(huì)知道自己在讀的是歷史。但是組成社會(huì)科學(xué)的不同要素—有時(shí)是這種,有時(shí)是那種,有時(shí)又是另一種模式—使我們?cè)陂喿x任何有關(guān)社會(huì)科學(xué)的作品時(shí),很難回答這個(gè)問(wèn)題。事實(shí)上,這就跟要給社會(huì)科學(xué)下定義是同樣困難的事。
不過(guò),分析閱讀的讀者還是得想辦法回答這個(gè)問(wèn)題。這不只是他要做的第一件工作,也是最重要的工作。如果他能夠說(shuō)出他所閱讀的這本書(shū)是由哪些要素組成的,他就能更進(jìn)一步理解這本書(shū)了。
要將一本社會(huì)科學(xué)的書(shū)列出綱要架構(gòu)不是什么大問(wèn)題,但是要與作者達(dá)成共識(shí),就像我們所說(shuō)的,這可是極為困難的事。原因就在于作者無(wú)法將自己的用語(yǔ)規(guī)則說(shuō)明清楚。不過(guò),還是可以對(duì)
關(guān)鍵字有些概括性的了解。從詞義看到主旨與論述,如果是本好書(shū),這些仍然都不是問(wèn)題。但是最后一個(gè)問(wèn)題:這與我何干?就需要讀者有點(diǎn)自制力了。這時(shí),我們前面提過(guò)的一種情況就可能發(fā)生—讀者可能會(huì)說(shuō):“我找不出作者的缺點(diǎn),但是我就是不同意他的看法。”當(dāng)然,這是因?yàn)樽x者對(duì)作者的企圖與結(jié)論已經(jīng)有偏見(jiàn)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