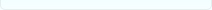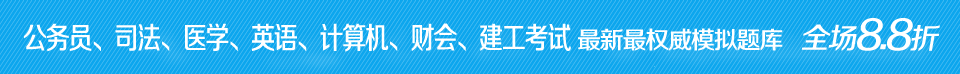書肆,《辭海》解釋為“書店,古代稱書店為書肆”。此定義較為片面:《論語·子張》云:“百工居肆,肆,即是作坊。《漢書·食貨志》:“開市肆以通之”。肆,即是集市貿(mào)易的地方。由此可見,書肆既有指賣書的店鋪,又有指刻書的作坊的意思,或二者合而為一,兼而有之,如古籍中的“酒肆”、“茶肆”之謂相同。
關(guān)于書肆,現(xiàn)今能見到的最早記載,來自西漢末年的哲學(xué)家、文學(xué)家、語言學(xué)家揚(yáng)雄,在他的《法言》一書中,曾提到“好書,而不要諸仲尼,書肆也;好說而不要諸仲尼。說鈴也。”春秋以前,書籍少且笨重,大都集中在少數(shù)貴族手里,即使學(xué)識淵博如孔子,要學(xué)周禮,都得向掌管典籍的周史官老子請教。孔子是興私學(xué)的第一人,但他“述而不作”的主張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典籍的豐富與發(fā)展。依賴師徒授受、口耳相傳的教育方式隨著書肆的出現(xiàn),呈現(xiàn)出豐富多彩的形態(tài)。
漢代造紙術(shù)的改良,使得書寫更加便捷;唐代雕版印刷術(shù)的發(fā)明,為書籍的大量復(fù)制帶來了福音,也為書肆的發(fā)展注入了新的活力。在當(dāng)時經(jīng)濟(jì)文化比較發(fā)達(dá)的城市,如長安(今陜西西安)、洛陽(今河南洛陽)等地,書肆如雨后春筍般涌現(xiàn)出來,在完成流通圖書的本質(zhì)使命同時,書肆也成為貧寒讀書人增長知識、踏上仕途的階梯。
東漢哲學(xué)家王充,就是這樣一位從書肆里學(xué)得滿腹經(jīng)綸的貧寒學(xué)子。據(jù)《后漢書》記載,王充小時候家里很窮,買不起書,所以他經(jīng)常游走于洛陽的大書肆,翻閱那里所賣的書籍,加上他是個
博聞強(qiáng)記的人,憑借
過目不忘的本領(lǐng),硬是把看過的諸子百家著作融會貫通,終成大家。
也有記性不好的,清朝詩人袁枚就沒有王充那樣的好記性。同王充一樣,袁枚小時候也遭遇了沒錢買書的困境,每次放學(xué)回家路過書肆的時候,他都要如饑似渴地翻閱架上待售的書籍,碰到便宜的就買回家看,如果是價格昂貴的大部頭,就只能望而卻步了。所謂日有所思,夜有所夢,到了晚上,袁枚還常常夢到書肆的經(jīng)歷,為此他專門寫了一句詩:“塾遠(yuǎn)愁過市,家貧夢買書。”聊以自嘲。正是這段經(jīng)歷,促使成名后的袁枚買書藏書成癖,但買回來后大都束之高閣,可見“書非借不能讀也”確有其事。
對于貧寒學(xué)子來說,身居大都市的可以去書肆看書,而生于偏遠(yuǎn)地區(qū)的就只能去借書了。五代后蜀宰相毋昭裔小時候很窮,曾向友人借閱《文選》,當(dāng)時雕版印刷還沒有廣泛用到刻印文史書籍上,手抄本《文選》顯得格外珍貴,所以那人面有難色,不是很樂意借。受此刺激,毋昭裔更加發(fā)奮讀書,并許下誓言,他日發(fā)跡后一定要刊印《文選》,使天下貧寒之士受益。為官后,毋昭裔并沒有忘記自己的誓言,他刻印了《文選》《初學(xué)記》“九經(jīng)”等書,大大豐富了后蜀圖書市場。這種看似意氣用事的舉措,既開創(chuàng)了私人刻印圖書的先河,也在客觀上為四川地區(qū)的文化發(fā)展做出了不小的貢獻(xiàn)。
隨著時代的發(fā)展,書肆的名稱不斷發(fā)生著變化,陸續(xù)出現(xiàn)了書林、書鋪、書棚、書堂、書屋、書經(jīng)籍鋪等名稱。宋代以后,書坊逐漸取代書肆,成為書店的新代名詞。而今,隨著商品經(jīng)濟(jì)的發(fā)展,各大實(shí)體書店受到電子書籍的沖擊,經(jīng)營壓力巨大,但方法總比困難多,我們的書商們也積極應(yīng)對想出了靈活多樣的經(jīng)營方法,受到各類讀者歡迎。